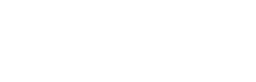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
高校规划编制,必须以变局中的“战略判断力”取代惯性中的“路径依赖”。“十五五”周期已不同于往昔的线性增长阶段,它标志着高校发展步入一个结构性重塑与系统性重构的时代。在这一阶段,高等教育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跃升,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突破。规划不再是常规事务的整理,而是战略能力的体现,是组织对未来深层变动的判断与布局。高校唯有在理念上真正突破“增设几个学科”“砍掉几个专业”“提高几个指标”的路径依赖,才能回应这个时代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,将规划工作转化为识变、应变、求变的内生机制。
全球格局的深度震荡,为高校发展塑造了高度不稳定的国际环境。当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空前加剧。大国博弈日趋常态,科技脱钩、数据管制、人才流动限制等非传统风险加速蔓延至高等教育领域。美国对华科技限制已不局限于产业界,更直接作用于高校的科研合作、师生流动和学术话语体系。在这一背景下,传统以“开放换成长”的发展逻辑面临挑战。高校需在保障国家利益、拓展国际空间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,重构与全球知识网络的连接方式,推动更加多元、对称、韧性的国际合作新范式。
技术革命的全面推进,正倒逼高校重构知识体系与能力边界。人工智能、生物合成、量子科技等引发的技术突变,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穿透学科边界与教学体制。高校传统学科体系、课程结构、人才培养模式正在遭遇系统性挑战。教育场景中的AI赋能,不只是工具替代,而是范式革新:它重塑教学流程、组织结构、学习关系,推动高等教育从“知识传授”为核心向“能力建构—思维训练—价值引导”系统转向。高校在“十五五”期间,必须对照技术演进趋势主动调整教育架构,避免边改革边落伍的被动局面。
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战略新主轴,高校需主动定位自身功能角色。新质生产力不是抽象口号,而是对人才、知识、技术、制度之间深度耦合的现实召唤。高校必须从“知识供给者”转向“创新驱动者”“平台组织者”和“结构转化者”,承担起基础研究策源、技术转化枢纽与复合型人才培育中心等多重角色。这要求规划编制环节不仅要提出若干创新任务,更要从系统结构上构建支持“交叉研究-场景转化-组织协同”的制度生态。唯有精准嵌入新质生产力链条,高校才能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。
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对高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“结构性适配”要求。“十五五”期间,地方经济发展正从普遍追求规模扩张转向结构重组、质量跃升。这一转向直接作用于高校专业结构、服务模式与供给逻辑。传统“靠上拉、靠下沉”式对接方式难以为继,高校必须精准识别所在区域的战略产业转型方向、技术路线演化趋势与高技能人才缺口,从而在规划中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适配与生态共生。否则,即使高校“发展良好”,也可能被区域经济的变轨甩出主赛道。
人口结构与社会心态的变化,正在深层改变高校育人的价值基础。出生人口下降与青年代际观念转变,正深刻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动力、选择倾向与价值判断。“不内卷”“要意义”“重平衡”成为广泛认同的价值取向,这对高校传统的“统一路径-标准答案-排名导向”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根本性挑战。高校必须正视学生主体性与多样性需求,以更加弹性、开放、自组织的机制重构育人体系。这不仅关乎“怎么教”,更关乎“为什么教”“教什么人”,是“十五五”规划必须直面的问题。
教育公平与分层机制的紧张关系,要求高校构建更加包容的制度环境。在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中,公平与效率、流动与分层的张力日益突出。高校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沿场域,既是选拔机制的执行者,也是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。然而在实践中,过度排名化、资源垄断化、标准单一化的趋势,正在压缩教育的开放性与可及性。“十五五”规划应主动设定更加公平、透明、多元的入学路径、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,在制度设计层面扩大公平增量,以回应日益增长的社会期待。
发展和改革需要统筹兼顾,高校内部治理能力成为规划能否落地的决定性变量。高质量规划不是写出来的,而是治出来的。许多高校“规划目标宏大,行动方案空泛”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机制支撑力不足。组织协调碎片化、资源整合缺乏系统性、改革意志无法形成共识,导致“战略漂浮症”反复发生。因此,“十五五”规划不能仅停留在目标设计,还要统筹制度供给、组织能力与行为转化,形成“规划-改革-评估-预算”一体联动的治理生态。这是从“写一本好看的规划”迈向“办一所有力量的大学”的根本转折。
战略时代呼唤战略思维,高校必须以系统性洞察引领未来布局。“十五五”不仅是一个时间节点,更是一个范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。面对科技突破、产业重构、价值多元、信任重建等交织变量,大学不能再做趋势的跟随者,而应成为社会变革的预判者与组织者。这要求高校以更大的视野看待自身定位,以更强的组织力回应系统挑战,在全球高教格局的变动中确立具有穿透力与组织力的发展逻辑。真正具备前瞻性判断力的高校,将在这场历史转向中实现自身角色与价值的跃迁。
(来源:里瑟琦科教观察微信公众号)